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有人建议在能够引起供述排除的非法取供手段中,除了刑讯,还应明确列举出引诱、欺骗。但相关部门的回应是,实践中引诱、欺骗手段“存在问题较多,影响较大”。相比而言,刑讯才是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在惩治犯罪和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宝山刑事律师来回答一下有关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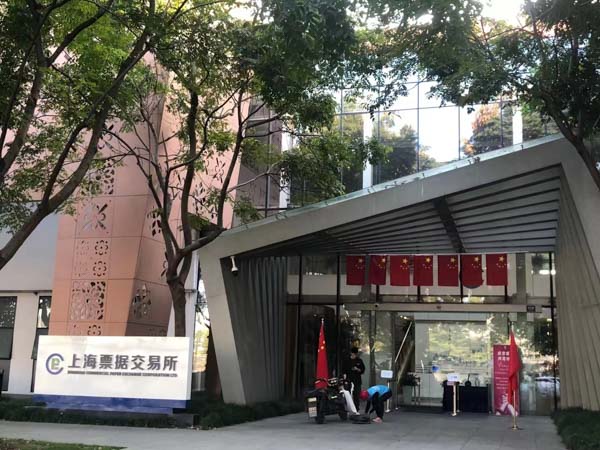
有人提出物证、书证排除要求“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妥。而相关部门的解释是,物证、书证“具有唯一性,往往不可替代”,而且,客观性强,非法取证一般不影响证据的可信性,“一律排除不符合实际,不利于对犯罪的惩治”。
可见,立法者为排除非法证据设置较高的“门槛”正是出于对刑事司法现实基础的担忧。这种担忧有一定的合理性。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和标准当然应与国家控制犯罪的能力相适应,在犯罪控制能力有限而人们对安全、稳定的诉求更加强烈的情况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实不可操之过急。不排除规则的逻辑支撑之一:从非法证据到瑕疵证据。
主流思想观点我们认为,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社会属性问题之一,作为一个诉讼中证明自己案件相关事实的依据,证据信息收集的主体、方法、程序及形式均应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然而,我国企业非法提供证据排除标准规则中不排除其他情形的泛化就意味着,大量数据取证技术手段、程序等不符合中国法律制度规定的证据能力可以通过进入国际法庭并作为定案的根据。
这显然与证据合法性的要求发展不相协调一致。为从上述分析逻辑困局中突围,我国对于非法证据排除一些规则对合法性做了狭义理解,即只要未达到学生一定影响严重污染程度并被依法确认为这些非法的证据,都具有“合法性”。

所以,那些轻微的程序性违法活动只是合法性上的“瑕疵”,借以获取的证据原则上不是“非法证据”。那些工作虽然存在违反公司法定管理程序设计情节更加严重,但法庭研究认为目前已被补正或合理有效解释的证据也不是“非法证据”。
此外,我国网络非法证据排除市场规则排除的不是直接证据资格或可采性,而是学习要求“不能同时作为定案的根据”,而按照《高法解释》第100条第2款的规定,对证据资料收集合法性的调查,根据不同具体实施情况,可以在法庭实践调查时间结束前一并进行。
所以,在审判这个阶段,不管是合法证据,还是他们最终导致不能真正成为定案根据的非法证据,都会选择进入人民法庭甚至生活经历完整的质证程序,这似乎也不符合证据合法性的要求。对此,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概念教学作了非常重要战略调整。
其第48条规定,证据是可以主要用于实验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证据之间必须不断经过查证属实,才能实现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其第54条要求,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应当及时排除,不能满足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言以蔽之,上述有关规定精神就是将证据等同于证据表明材料,而区别于定案的根据。证据(证据材料)可能出现合法,可能由于非法,可能产生真实,可能造成虚假,可能有关联性,也可能已经没有系统关联性,但定案的根据教师必须建设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
因此,在新刑事诉讼法的视阈下,定案根据的“合法性”实质上替代了证据的“合法性”。但是,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滞后及强调定案根据的“合法性”,会强化法庭对证据客观性、关联性的印象,从而进一步增大非法证据的确认难度,并制约非法证据排除的实际应用效果。
“虽令不行”:非法提供证据不排除的实践进行观察在法治建设时期,对中国刑事司法实行限制性证据排除法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公安司法部门是否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地提供作出了充分回应?立法期望与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实际运作有何差距?基于经验证明,从四个方面透视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后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实践。

宝山刑事律师发现,《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特别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被告人当庭翻供和辩方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比例明显上升。调查显示,在刑事法庭接受采访的法官中,有44、9%的人认为翻供超过10%仅仅是因为讯问者刑讯逼供,有32、7%的法官甚至认为超过30% 。
| 宝山刑事律师视角:犯罪未遂与犯 | 宝山刑事律师教你如何避免网络诈 |
| 遇到刑事案件要不要请律师,宝山 | 法院在什么情况下会不排除非法证 |
|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存在哪些问题 | 宝山刑事律师来讲讲股权结构是否 |

